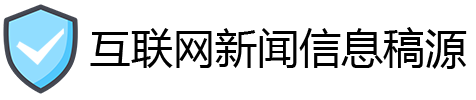讀者在海報前合影。

馬伯庸分享趣味故事和寫作經驗。

手持門票,走進故事。
文/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彭寧 龍俊玉 通訊員 向菲 圖/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田華
穿著最基礎的白T恤和深色褲子,45歲的馬伯庸親切得就像鄰家一位大哥哥,出現在湘西讀者面前。
9月24日晚,容納600余人的吉首大學演奏廳座無虛席,作家、編劇馬伯庸以《歷史中的大與小》為主題,與湘西文學愛好者展開分享。
他一上來就講了個身邊的小故事:如何用一個極富畫面感的敘述,巧妙說服母親不再催促他生二孩。他笑著引出主題:“人常常記不住道理,卻記得住故事和畫面。講道理不如講故事,歷史也一樣。”
大歷史里的小故事
整場分享,馬伯庸其實都在做一件事:講故事,講大歷史中那些被塵埃掩埋的小故事。
第一個故事關于高僧玄奘的“歸鄉淚”。
玄奘西行取經,是位名垂青史的“大人物”。但馬伯庸并未重述他穿越沙漠的艱險或譯經弘法的偉業,而是將他還原為一個離家四十多年的普通游子。五十歲時,玄奘重返故里,卻發現唯一的親人只剩一位老姐姐。在父母墳前,他“追惟平昔,情不自寧”,痛哭失聲。
“那一刻,他不是高僧,只是一個想念父母的孩子。”馬伯庸說,“我們總以為歷史人物是‘神’,但他們也會哭、會想家、會脆弱。人性才是最大的公約數。”
第二個故事,關于一封兩千年前的家書。
出土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的這兩封信,被稱為“中國最早的家書”。兄弟二人在信中問候母親安康后,便“圖窮匕見”地開始要錢要物。“母親,寄點錢和夏衣來啊!”“絲布太貴,直接寄錢就好!”“千萬別寄太少!”馬伯庸笑問:“這語氣,是不是像極了今天的大學生月底向爸媽‘求救’?”
然而,信的結局令人唏噓——它們是在大哥“衷”的墓中被發現的。黑夫與驚,最終很可能戰死沙場,再未歸家。“‘一將功成萬骨枯’,我們常常只記得‘將’,卻忘了‘骨’。而歷史,正是由無數這樣的‘骨’支撐起來的。”馬伯庸說。
第三個故事,來自兩塊磚。
在成都武侯祠的“大三國志展”上,馬伯庸注意到兩塊銘文磚。一塊燒制于公元170年,磚匠刻下“倉天乃死,當搏”抒發受壓之憤——這比黃巾起義的著名口號早了14年。另一塊刻于公元280年,一位姓朱的老匠人寫下“晉平吳 天下太平”,為戰亂終結而欣喜。
“亂世的開始與結束,不是單由史官決定的,更是由一個個普通人感知、記錄并推動的。”馬伯庸說,“磚匠不會寫史書,但他們用最樸素的方式,留下了時代的情緒。”
小故事里的大人性
為什么這些微小的故事能深深打動我們?馬伯庸的答案簡單而深刻:因為人性亙古不變。
“科技會變、制度會變、朝代會更迭,但人對親情的眷戀、對壓迫的反抗、對太平的渴望,是跨越時空的共鳴。”
玄奘的眼淚、黑夫要錢的家書、磚匠的刻字——這些細微的情緒,恰恰是歷史最真實的體溫。馬伯庸稱之為“歷史的溫度”,并視之為理解歷史的鑰匙。
馬伯庸坦言,他并非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,也寫不來帝王將相的權謀史詩。“我做了十年上班族,最懂的就是普通人的喜怒哀樂。”正是這種“普通人視角”,讓他的講述格外具有親和力。
他進一步闡發自己的“人民史觀”:歷史并非少數英雄書寫的宏大敘事,而是無數普通人愿望與行為匯聚成的長河。“每一個小人物單看都微不足道,但當千千萬萬人產生同一種訴求、同一種愿望,這種合力就會形成歷史的趨勢,推動時代向前。”
他認為,關注歷史中小人物的遭遇、選擇與作為,實則是在觸碰歷史的本質。“從細節看到人性,從小看到大,帶著這樣的溫度與同理心回望歷史,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歷史從何處來,向何處去。”
互動環節,有讀者問及如何面對人生逆境。馬伯庸分享了自己的寫作起點:最初是為賺稿費,而《風起隴西》的創作,竟是為了躲避畢業論文。“逆境或許會逼你走出另一條路,而那條路可能更適合你。”
談及湘西城市文化品牌塑造,他建議:“湘西文化底蘊深厚,但今天講故事不能只停留在表面,需洞察人性共通之處。只有講清楚人性,才能打通古今,打動不同時代的人。”他認為,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文旅發展的寶貴素材,而關鍵在于“激活它們,找到其在當代的價值所在”。
分享會在掌聲中落幕,關于“小人物”與“大歷史”的思考,已在許多讀者心中悄然生根。
記者手記
讀與思,聚成光
團結報全媒體記者 彭寧
許多次讀馬伯庸的書,總忍不住驚嘆于他構思的精巧、視角的新奇與情感的動人。合上書頁時,一個問題總在心頭縈繞:他究竟是怎么想到的?他是吃什么長大的?
9月24日晚,聽完馬伯庸近一小時的分享,那個盤旋已久的問題,似乎有了答案。
答案說來平常,無非是“讀與思”。
比如,他從云夢睡虎地秦簡中的時間與地點信息,推斷寫家書的兄弟倆參與的應是秦滅楚之戰中的淮陽之戰——那是秦國統一進程中關鍵且慘烈的一役,李信率二十萬大軍攻楚卻遭慘敗。兄弟倆很可能寄出信后就戰死沙場,留守家鄉的大哥才會將這兩封浸透烽煙的家書帶入棺槨,盼望著在另一個世界與魂牽夢縈的弟弟團聚。
再如,他從“江乘”這一地名在孫吳建立后便廢棄不用的細節,推測出在磚上刻下“晉平吳 天下太平”的朱姓匠人當時至少已六十歲。那六十年,正是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無雞鳴”的三國亂世,“天下太平”成了顛沛流離中人們最樸素也最堅韌的期盼。
這些常人難以察覺的視角,這般抽絲剝繭的觀察與感悟,究竟從何而來?
我想,這絕非一時靈感,而是源于一個龐大認知系統的支撐。那是一個由海量閱讀與深度思考構筑起來的精神宇宙,讀過的每一本書、每一次認真思索,都如一顆被點亮的星辰,彼此聯結,運轉不息。
在這一系統的支撐下,他所見所感的每一粒歷史塵埃——古籍中一句閑筆、文物上一道刻痕,甚至生活中某個荒誕的瞬間——都能被瞬間激活,與萬千知識節點鏈接、碰撞,迸發出新的線索、維度與故事。
于是,我們才看到他從《明史》中關于太子朱瞻基一段近乎敷衍的記載里,演繹出《兩京十五日》中那場沿運河奔命的絕地求生;從“一騎紅塵妃子笑”的詩句背后,洞察到“一事功成萬頭禿”的艱辛內核,寫就《長安的荔枝》中關于算法、物流與人性的敘事;從華山醫院院史館泛黃的檔案里,挖掘出《大醫》中一代醫者在時代洪流中的悲歡與堅守。
而反過來,這些不斷誕生的新視角、新故事,以及創作過程中必須進行的考據與思辨,又如同回流的能量,持續充盈、滋養甚至重構著原有的認知系統。
系統滋養靈感,靈感反哺系統——這就形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循環,推動認知邊界與敘事可能不斷拓展。
我想我找到了答案:馬伯庸是吃“書”長大的。
一本一本地讀,一層一層地思,筑起屬于個人的精神宮殿。再用這座宮殿里孕育的光,去照亮歷史被遺忘的角落,讓沉寂的塵埃重新發聲、長出筋骨,成為一個個活色生香的故事。
或許我們不必再驚嘆天才遙不可及。答案,就藏在最樸素的道理里:無非是苦讀的耐心、思考的韌性,是讓知識在腦中不斷聯結碰撞的自覺。
這條路漫長而孤獨,但唯有如此,靈感才能如泉奔涌,照亮來路與前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