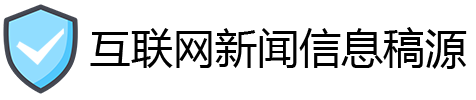盧瑞龍
1
今日,收到兩本書。
一本叫《巴代》,是國家一級作家龍寧英大姐的長篇小說新作。
一本叫《保靖縣民族文化藝術史料匯編》,是耄耋的學者、作家彭圖湘先生任執行主編的碩果。
兩本書,我都歡喜。兩本書,都是至寶。
2
是中午時,彭圖湘先生站在我的樓下,說:佬佬,你快點來取書啊,還要我等你。
我亟亟奔下樓。細雨里,他像一株老去的杉或松。他的華發,齊齊地向后翻梳著,又被雨水,點上了些些摩絲,晶亮晶亮的。書被揣在懷里,他身板略略前傾,像為書撐開的一把小小的傘。
忽忽,我的嘻皮笑臉里,就生出了絲絲心疼。想起從前蹉跎的年月,他一度對年少輕狂的我說:佬佬,你醒醒咯,你動動筆呀,寫點兒東西好不好?我的鼻子就有點兒發了酸。幸好,我不必讓淚水掉下來,因為,細雨它乖巧,它柔滑不斷,它撫摸了我的顏面。
3
作為苗族的優秀女兒,龍寧英大姐的文字,一直在苗嶺的深處纏綿、飛揚。在我有限的閱讀里,讓我動容的作品并不是很多,但是,她的文字算。
她的文字,那么純、那么淳。關于苗家大地,關于苗民族,她的臍帶,從未被割斷。那個古靈精怪的苗家女孩兒,她貼近苗民族的苦難深重胼手胝足,也貼近苗民族的翻天覆地日新月異;她寫暗黑黑的貧窮,也寫亮堂堂的富裕;她歌,也舞;她哭,也笑。一切的年長月久啊,紫云英看得見,馬桑樹也看得見,古苗河看得見,十八洞也看得見。而這本厚厚的《巴代》,想必,我會徐徐舒舒地看得見她筆下心底的千千結、萬萬結吧?
想起那年,我揣著她的作品《柳蒲寨流過蘇麻河》,去了貴州松桃,在黔東草海,在盤信小鎮,在歐百川故居,在蘇麻河畔,我流連了好久好久。我吹草海的風兒,我品小鎮的小吃,我凝眸先驅的雕塑,當我掬起又掬起蘇麻河的清流時,我的心,比岸邊的柳,更搖曳,更輕柔。那次順著她腳步的另一種重走,雖是浮光掠影、走馬觀花,但是,她的文字,卻被鐫刻在了我的骨子里,再也沒有褪色、泛黃。
更讓我覺得巧而幸福的是,我的孩子考取了銅仁學院,正在我歡喜的黔東大地,她筆下的黔東大地,做夢并且追尋。這樣宿命里的契合,多少次,是啊,多少次,讓我在接送孩子的空隙里,美好而生動不已。
4
這本《保靖縣民族文化藝術史料匯編》,就我所知的,全然是彭圖湘先生的獨獨所有。都說,甘苦寸心知,我想,是呢,是呢。
編完了這本,我也了卻了一個心愿,可以松口氣了,他這樣對我說。我是完全理解的,或者說,我是由著他的。從前多少次,我對他說,上年紀了,功成名就了,該享享清福了。但說只是歸說,說了也是白說。當眼下,是的,眼下,我看見他和另外幾位古稀耄耋的先生戴著老花鏡,在縣民中修志辦里忙活的身影時,我自己都改變了活到古稀之年就偃旗息鼓、馬放南山的小心思,轉而想,哪天,眼睛看不清了,手也不能動了,就不做了。用書面語說,就是,生命不息,奮斗不止。
親撫著這本書,這本厚重的書,就像撫摸著他的鼻息,仰望著他的項背。他的如椽之筆,奔越過保靖的山川大地,梳掠過歲月的煙云風雨,在我們的面前,展現出一幀又一幀璀璨斑斕的珍稀瑰麗。這是山水的幸運啊,這是我們的幸運。
從下放的山野之民,靠著單相思的一支筆,寫進鄉文化站,寫進縣文化館,寫進縣作協、州作協、省作協及至中國作協,想來這一路的跌撞、奔突,該有多艱辛,又該有多榮耀。
相識一場,算算幾近四十年了,由陌而友,又如兄,又如父,也吵也鬧,也曾鐵青著臉,要斷交,可是這情緣,怎么會,斬得斷。這是我們的共情,這是我們的共生。
5
我被錯愛,我被厚愛。
說一千遍謝謝,那都太短,那都太淺。
不如,用盡愛和心,努力寫出真正的文字呀。努力為這偶然的一生和人世,種下花兒,種下馨香,種下芬芳,哪怕,哪怕只有一朵,一抹呢?